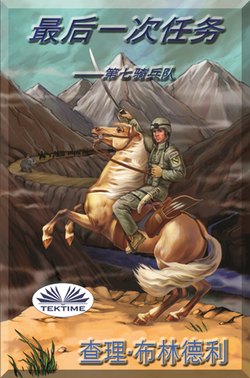Читать книгу 最后一次任务 - Charley Brindley - Страница 11
第十章
Оглавление当他们走进离河边营地两英里远的小空地时,天几乎黑了。
“天啊,”沙拉科娃说,“他怎么了?”
“他被折磨过,”亚历山大说,“一种缓慢而痛苦的死亡。”
队里的的六名成员,连同丁丁·班·苏妮娅和利亚达一起,站在那里低头看着尸体。小队的其他人和卡瓦尔斯基都留在了营地。
十几名步兵在附近等候,观察周围树林的情况。
秋儿从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一条黄色和蓝色的围巾,盖住上尉的生殖器,至少是剩下的部分。
“该死的畜生,”她一边把围巾披在他身上,一边低声说道。
“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在路上杀了很多人吗?“沙拉科娃问道。
“不,”亚历山大说,“他已经死了几天了。我认为他们在他刚降落时就杀了他。”
“他们一定看到他从空中降落地面,并在他落地时将他抓住,”秋儿说,“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他?”他遍体鳞伤。
“我不知道,”亚历山大说,“但我们得把他埋了。”我们的兵力不足以击退一次大规模的进攻。”他扫视了一下昏暗的树林。“不能在这久留。”
沙拉科娃说:“我们不能把他光着身子埋葬。”
“为什么不呢?”洛贾布问道。“他就是这样来到这个世界的。”
“我的背包里有一条聚酯薄膜毯子,”华金背对着沙拉科娃说,“在侧袋里。”
当她取下紧紧折叠的毯子时,一个长东西从他的包里掉了下来。“哦,对不起,华金。”她跪下来捡起来。
丁丁·班·苏妮娅注意到了闪亮的乐器,她的眼睛睁大了。她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利亚达。利亚达也看到了,很明显他们俩都想问这个问题,但觉得现在不是时候。
沙拉科娃把乐器递给华金,华金拂去抛光金属上的灰尘,然后对她微笑。“没关系。”
她把银色的毯子铺在地上,其他人开始用锋利的刀子弄松泥土。他们开始用手挖坟墓。丁丁和利亚达帮忙,很快这个洞就有3英尺深,7英尺长。
“那就可以了,”亚历山大说。
他们把上尉的尸体放在毯子上,然后包在他身上。在他们轻轻地把他放进坟墓后,秋站在坟墓边上,摘下了她的头盔。
“仁慈的主啊......”
其他人摘下头盔,低下了头。利亚达和丁丁他们站在一起,低头看着尸体。
秋儿完成了主的祈祷,然后说:“主,我们现在将我们的朋友兼指挥官推荐给您。阿们。”
“阿门,”其他人说。
“班长,”华金举起从背包里掉下来的闪亮的笛子,低声说道。
亚历山大点点头,然后华金把笛子放到唇边,开始演奏拉威尔的《波莱罗》。当忧郁的音乐飘过暮色中的空地时,其他士兵跪下开始用一把把泥土填满坟墓。
利亚达也跪了下来,帮助掩埋死去的上尉。
只有丁丁·班·苏妮娅和华金还站着。当丁丁惊讶得张大嘴巴盯着正在演奏音乐的华金时,她的右手好像是自然地移动,就像一个盘绕的生物在她背后的皮革钱袋里盲目地摸索着什么。她拿出十一年前在迦太基制作的旧木笛。
华金注意到了这个动作,看着她用指尖拿着长笛。他的手虽然伤痕累累,但却很有力,在银色的琴键上跳着一段优美的芭蕾舞。丁丁一直等到他停下来,然后她把笛子放到唇边,开始演奏。
其他人似乎没有注意到音乐的音符,因为他们正在努力填充坟墓,但华金肯定注意到了–她正在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准确地弹奏着《波莱罗》,就像他刚才弹奏的那样。他又开始了他的音乐,与她在歌曲中的节奏合拍,但比她低一个八度。
秋儿看了看丁丁,然后又看了看华金。她微笑着,泪水顺着脸颊流下,然后她抚平桑德斯上尉墓上的泥土。
当他们回到营地时已经过了晚上9点。
“我们去找卡特里,”利亚达说着,随即和丁丁转身离开了第七骑兵队的士兵。
“好的,”卡琳娜说,“回头见。”
* * * * *
那天晚上,篝火旁是一个阴沉的夜晚。当其他人在处理桑德斯上尉的后事时,卡瓦尔斯基已经醒过来了。他感到剧痛,但当秋儿问他是否想再注射一针吗啡时,他摇了摇头。
“那东西让我大吃一惊。没有它我也能活下去。”
卡琳娜告诉卡瓦尔斯基上尉已经被折磨死了。
“该死的,”卡瓦尔斯基说,“现在我很高兴我们杀了20个讨厌的狗娘养的。”
卡琳娜说:“你是说几百个人吧。”
“我说的是我和利亚达。伙计,她擅长弓箭。当她箭尽粮绝的时候,她从地上抓起我的步枪,把它当作棍棒用。
“是的,”卡琳娜说,“战斗结束后,我帮助找回了她的箭。她当时如死一般的。”
富西利尔从武器箱中拿走了一些快餐。“谁想要7号菜单?”
洛贾布举起他的手,然后她把它扔给他。
每个人都坐在篝火旁的木墩上。
“12号菜单?”
“我要这个,”沙拉科娃说。
“20号菜单?”
没有人对冷饭很有热情,但是其中一些人试着拿它填饱肚子。
“嘿,班长。”
“嗯,斯帕克斯。”
“看谁来了。”
亚历山大看见一辆货车驶向他们。“看起来像卡特里。” 他站起来,弹掉裤子上的尘土。
“她身边还有一个人,”富西利尔说。
“是丁丁和利亚达。”
当他们停下来时,秋儿过来迎接了他们。“你好。”
“你好,”丁丁说。
利亚达从马车上跳下来,走向挣扎起身的卡瓦尔斯基。
“给我手臂。” 利亚达拉住他的手臂,将手臂放在她的肩膀上。
“是的,我确实需要帮助。”他紧紧抓住了她,蹒跚地迈出脚步。
“来看看。” 她把他扶到马车后面。
“哇,”卡瓦尔斯基说,“嘿,伙计们,过来看看这个。”
马车床上放着一个大铁锅,里面盛满蒸熟的谷物和大块的肉。在它旁边是十二个圆形的面包,以及几个用圆木雕刻的碗。
卡特里伸手将锅拉到货车床的边缘,然后失手将两个长木柄从锅侧面的金属环上滑了下来。
“过来,”亚历山大说,“让我来帮助您。”
当他们合力抬起锅并抬到火上时,她说了些什么,听起来像是“随便吧”而不是“谢谢”。
“饭真香,卡特里,”在他们将锅抬下来放到火旁边的地面时,亚历山大说道。
当她从锅中取出木柄并把它们放到马车上时,卡特里耸了耸肩,从脸上撩起一缕赤褐色的头发。亚历山大看着她朝着篝火走去,她在那儿解开了脖子后面的皮绳,让头发散下来。她的头发密而长,发亮的棕色秀发垂在肩膀下面。她用牙齿咬着皮绳,将松散的发束聚拢在一起,然后把头发扎在后面。当利亚达和丁丁将大块面包切成小块,并和从锅里拿出的碗一起互相传递时,她走到亚历山大的身旁,去帮助她们。
“我们很难过,”丁丁用手语说道,“因为你们失去了桑德斯。”
“谢谢你。”秋儿做了手势说,“我们所有人都感谢你和你的人员对我们的帮助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我们的人?”
“嗯,他没有......”她揉着脸颊,然后抚摸着她的头发。
嗯 是啊 他没有胡须。你们大多数男人都留着胡须。”
丁丁盛满了自己的碗,就坐在沙拉科娃旁边的一截圆木上。丁丁看着华金,目光和他对视微笑。他笑了,咬了一口食物。
“这是什么肉?” 秋儿问利亚达。
利亚达说了些什么,做了个手势。
秋儿摇了摇头。我不明白。
利亚达说:“丁丁。”然后问她一个问题。
丁丁想了一会儿,然后像牛一样哞哞叫。众人都笑了。
“啊,我们在吃哞哞肉,” 秋儿说,“一定是牛肉,或者也许是野牛。味道非常好。”
“太糟糕了,”卡瓦尔斯基说,“我想可能是......”他模仿一声嘶哑的马蹄声,然后用脚刨地。
丁丁,利亚达和其他人一起笑了。
佐尔巴·斯皮罗斯说:“我当时在想,汪汪。”
卡迪说:“或者也许是‘哞哞’。”
卡瓦尔斯基几乎被一口食物呛住了,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更多的笑声。连很少微笑的卡特里也嘲笑着卡瓦尔斯基。
卡琳娜抚摸了一下利亚达的脸颊。“他们为什么给您打上烙印?”
利亚达摇了摇头。“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“标记,为什么?” 卡琳娜抚摸自己的脸颊,耸耸肩膀。
坐在附近的丁丁听了他们的谈话。她与利亚达交谈,利亚达用希腊语向佐尔巴·斯皮罗斯询问这个问题。他解释说,卡琳娜想知道她如何在脸上留下印记。
利亚达抚摸伤疤说:“我做了标记。”
“你?”卡琳娜指着利亚达。“你是自己做的吗?”
利亚达点点头。
丁丁来到利亚达旁边坐下。“这是......嗯......”她抚摸着她的脸颊,她与利亚达拥有一样的标记,只是印在脸的另一侧。“不会说这个词。” 她做了一个用锄头农耕的手势,然后站了起来,像打鞭子一样打了个手势。
“奴隶?”卡瓦尔斯基问道,“她是想说‘奴隶’吗?”
卡琳娜说:“他们不可能成为奴隶。他们管理阵营,几乎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。”
卡特里坐在其中一截圆木的一端,对丁丁说,丁丁耸耸了肩膀。
卡琳娜说:“他们努力想办法告诉我们一些事情。”
华金站了起来,做了一个锄地的手势,然后搬运沉重的物品。他停下来擦拭额头,然后假装对附近某人感到恐惧。他抓住假想的锄头,重新开始工作。
“奴隶,”卡琳娜指着华金说。
“是的,奴隶。”丁丁说。
“你和利亚达是奴隶?” 卡琳娜问。
丁丁摇了摇头。“我是斯洛博的奴隶......”
“库斯别耶,”利亚达说,“库斯别耶·斯洛博(Sulobo,kusbeyaw)。”
“丁丁是奴隶,她是斯洛博的奴隶吗?”华金问道。
丁丁和利亚达好像点点头。
“是的,”卡琳娜说,“而且我们都知道库斯别耶是谁。”
“耶洗别(Yzebel),“利亚达做出了一个动作,从钱包中取出硬币,然后交给别人。
“耶洗别买了丁丁。” 卡琳娜说,“说下去。”
“ 斯洛博。”
“啊,耶洗别从斯洛博那儿买了丁丁。”
“是的,”利亚达说。
“丁丁几岁?” 卡琳娜问。“她是婴儿吗?” 她假装将婴儿抱在怀里,然后指着丁丁。
“不,”莉亚达说,伸出手比在胸部高度上。
“丁丁是个年轻女孩,耶洗别是谁?”
利亚达怀里抱着一个婴儿。
“耶洗别是个婴儿?”
“没有。利亚达是…嗯...”
“利亚达是个婴儿?”
利亚达摇了摇头。
华金说:“我认为耶洗别是利亚达的母亲。”
“哦,我明白了,”卡琳娜说,“耶洗别像婴儿一般摇动利亚达。耶洗别是你的母亲。”
利亚达举起两个手指。
“你有两个母亲?”
利亚达举起一根手指,然后是两根。她指着第二根手指,她说“耶洗别。”
耶洗别是你的第二个母亲。耶洗别从斯洛博那儿买了丁丁时,您是婴儿吗?”
“不。” 利亚达伸手比到胸部高度。
“耶洗别买下丁丁时,您还年轻?”
“是”。然后我们......”利亚达紧紧地抱着丁丁,向她倾斜着头。
“你们就像姐妹吗?”
卡琳娜举起两根手指,一根手指缠绕在另一根手指上。他们都点了点头。
“斯洛博做丁丁主人时给丁丁做了标记?” 卡琳娜问。
“是的,”利亚达说,“而且我认为我要像我的姐姐丁丁·班·苏妮娅一样,所以我做了同样的标记。” 她的手很清楚地讲述了这个故事。
卡琳娜闻了闻,擦了擦脸颊。“我不能......”
“想象吗?”华金说。
“我无法想象......”
“如此牢固的情谊,只因为姐姐被烙为奴隶而做烙印?”华金说。
卡琳娜点点头。
大家沉默了几分钟。
卡瓦尔斯基说:“一些强大的力量使我们简单的日常变得微不足道。”
利亚达说:“卡特里是斯洛博的奴隶。”
“你说什么?”亚历山大问。
“是的,”丁丁说。
亚历山大说:“卡特里,你是斯洛博的奴隶?”
卡特里对利亚达说了些什么,利亚达用他们的语言和她对话。然后,卡特里松开了束腰外衣的衣带,利亚把她背部的外衣向下拉一点,以使他们看到她右肩胛骨上的奴隶标记。
“该死,”卡瓦尔斯基说,“怎么会有人这么做?”
卡琳娜摸了摸伤疤。“太残酷了,但是她的标记牌与众不同。”
“是的,”华金说。利亚达和丁丁的干草叉轴上有一个箭头。卡特里的标记有干草叉,蛇缠绕在杆身上,但却没有箭头。”
“为何不同?” 卡琳娜问。
“这是一个管理标记,”卡瓦尔斯基说,“在古老的西部,当一头母牛被出售或被盗时,他们不得不将原来的标记更改为不同的标记。他们用一个管理标记来替代旧标记。丁丁和利亚达标记上的箭头是一个管理标记,它说明本人已不属于原主人。”
“这些妇女遭受牛一般的待遇。” 卡琳娜说,“就像动物一样被人交易。”
“斯洛博,”亚历山大说,“那个龟孙子。”
卡特里穿好了衣服,扎紧了衣带。然后转身离开他们。
“等等。”亚历山大拉起她的手臂阻止她。“别走。”
她面对着他。
“您不必成为奴隶。奴隶制在200年前就被废除了。”
卡特里瞥了一眼利亚达,然后利亚达向秋寻求帮助,以解释亚历山大所说的话。
“嗯,”秋儿说,“我怎么用手语说‘自由’。”
洛贾布打断了她。“我要从斯洛博那儿买她。”
“对啊,笨瓜,”卡迪说,“你只会像那样拥有一个女人,你这个蠢货。”
卡琳娜说:“我认为第七骑兵队不该拥有任何奴隶。”
洛贾布说:“你们这些笨女人,你们都因为没人愿意为你付钱气炸了吧。”
卡迪说:“狗屎,去死吧,二百五。”
“把它关掉,卡瓦尔斯基,”亚历山大说,“多余。”当他看着卡特里离开时说。